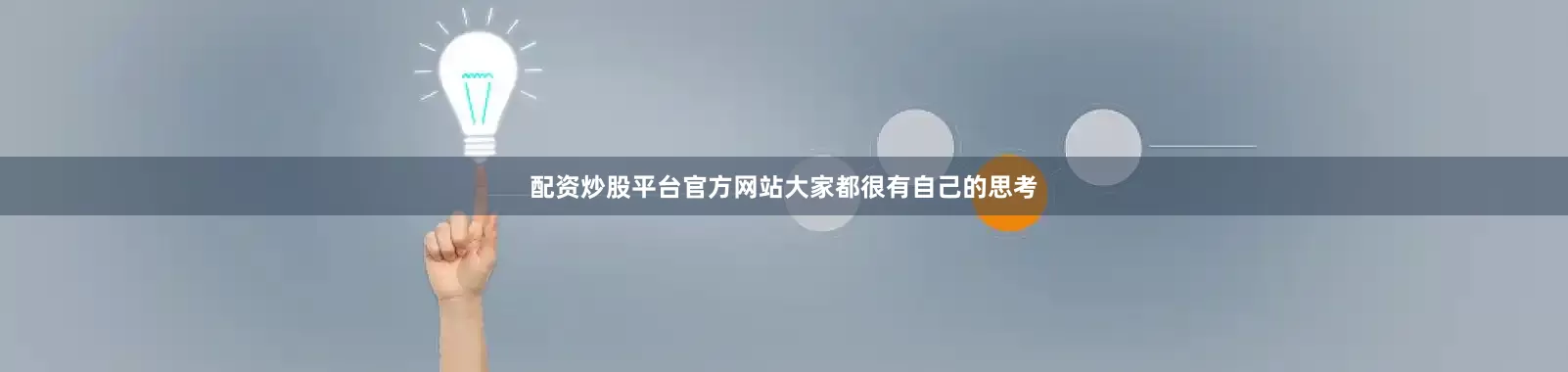一九八七年的夏天,热得邪乎。太阳像个烧透了的白炽灯球,从早到晚悬在头顶,把地上的一切都烤得打了蔫儿。村东头那条平日里还算有点气势的渭河,如今也瘦成了细溜一条,浑黄的河水有气无力地淌着,露出大片大片被晒得滚烫的河滩地。我的十亩西瓜田,就趴在这片河滩上。
那些西瓜秧子,是我一瓢水一瓢水伺候大的,叶子肥嘟嘟、绿汪汪的,在毒日头下硬是撑起了一片生机。一个个滚圆的、花皮大西瓜,就藏在那些叶子底下,悄没声地吸收着光热,酝酿着沙甜。晌午头,田里一丝风也没有,只有知了在没命地嘶叫,吵得人脑仁疼。我光着膀子,皮肤晒得黝黑发亮,汗水淌下来,在胸前冲出一道道泥印子。我正猫着腰,检查一个熟透的瓜,手指弹上去,发出沉闷的“嘭嘭”声。
就在这时,我听见田埂那头传来脚步声,轻轻的,有点犹豫。我直起腰,手搭在额前遮住光望过去。这一望,心口就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
是曾小燕。
展开剩余95%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小碎花裙子,裙子被汗濡湿了些,贴在身上,勾勒出姑娘家好看的线条。她站在田埂上,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她,脸蛋红扑扑的,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,有几缕头发被汗水粘在了白皙的脖颈上。她看着我这边的瓜地,眼神有些飘忽,双手紧张地捏着裙角。
我们村儿里,曾小燕是顶漂亮的姑娘,像一棵水灵灵的小葱。她爹曾老奎是村里的会计,家境比我这穷瓜农好了不知多少。小燕孝顺、勤快,提亲的人差点踏破她家门槛,可她爹眼光高,一心想给她找个吃商品粮的。
我愣愣地看着她,一时忘了说话。自从三个月前,我托媒人去她家探口风,被她爹拿着扫帚撵出来,骂我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、“穷光蛋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想娶媳妇”之后,我就再没敢正眼瞧过小燕。不是不想,是觉得臊得慌,也怕给她惹麻烦。
“小燕?”我迟疑地喊了一声,声音干巴巴的,“你……你咋来了?这大日头底下。”
曾小燕抬起眼看向我,那双好看的眼睛里,水汪汪的,藏着我看不懂的情绪,像是害怕,又像是下了什么决心。她没回答我的话,只是慢慢走了过来,走到我面前,离我只有几步远。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、带着点汗味的皂角香气。
地里的热浪一股股往上涌,知了叫得更凶了。她抿了抿嘴唇,胸口微微起伏着,终于开口,声音不大,却像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:
“李良,我怀孕了。”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好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田里的知了声、远处河水的流淌声,全都消失了。我只听见自己心脏“咚咚咚”地擂着鼓,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。三个月前那个晚上,月亮也是这么明晃晃的,我们在村后的麦草垛旁边……就那么一次……我手里捏着的那半截自己卷的旱烟,不知不觉被我捏得稀烂,烟丝从指缝里漏下去。
曾小燕说完那句话,就低下了头,脖颈子都泛着红,不是晒的,是羞的。她不敢看我。
我猛地想起了她爹曾老奎那张凶神恶煞的脸,想起他三个月前指着鼻子骂我的话:“李良你个王八犊子!再敢惦记我家小燕,老子打断你的腿!”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蹿上来,和浑身的燥热搅和在一起,让我打了个激灵。
但我看着眼前的小燕,她孤零零地站在这里,对着一个被她爹瞧不上的穷瓜农,说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话。她得鼓起多大的勇气?她以后要承受多少风言风语?我的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住了,又疼又涩。
几乎是没有犹豫,我哑着嗓子,脱口而出:“别怕。明天,明天我就去你家提亲。”
这话一说出来,我自己先怔了一下。去曾老奎家提亲?我想象着他抄起扁担把我打出来的场面,后脊梁一阵发寒。可话已出口,看着小燕骤然抬起的、带着一丝光亮和难以置信的眼睛,我心里那点害怕,突然就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压了下去。我是个男人,这时候不能怂。
曾小燕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,好像要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。忽然,她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,露出一个极浅、却让我心跳漏了好几拍的笑容。她侧过身,伸出纤细的手指,指向瓜田正中央那个我特意留种用的、最大最圆的西瓜,说:
“要是那个瓜甜,我就嫁。”
她的声音轻轻的,带着点姑娘家的娇嗔,又像是一种最后的试探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那个大西瓜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一瞬间,我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她不是真的要尝瓜的甜不甜,她是在给我一个台阶,也是在给她自己一个念想。
“好!”我应了一声,声音比刚才坚定了不少。
我几步跨进瓜田,朝着那个最大的西瓜走去。秧苗刮着我的腿,我也顾不上。走到那个瓜面前,它真大,像个青黑色的胖娃娃。我蹲下身,用手拍了拍,声音沉稳。可我抬起手,准备用手掌劈开它的时候,那只手却不听使唤地抖了起来,抖得厉害。不是因为没力气,是因为心里太乱了。这一瓜下去,劈开的好像不只是个西瓜,更是我和小燕往后的人生。
我深吸一口气,定了定神,手掌猛地落下!
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瓜应声裂成两半,露出红瓤黑籽,一股清甜的瓜香瞬间弥漫开来,冲淡了午后的燥热。瓜瓤沙棱棱的,熟得正好。我掰下一块最红的心儿,递给已经走到我身边的小燕。
她接过去,小小的咬了一口,慢慢地嚼着。阳光照在她低垂的眼睫上,投下一小片阴影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像个等待判决的囚徒。
过了一会儿,她抬起头,眼睛亮晶晶的,看着我,很认真地说:“真甜。”
我松了口气,刚想傻笑,却又听见她说:
“像你偷偷塞给我家的每一个瓜,都这么甜。”
我一下子愣住了,张着嘴,看着她说不出话。
她……她都知道?
那些事儿,我以为我做得神不知鬼不觉。自从喜欢上她,又自知家境配不上,我能做的,也就是偶尔把田里最好最甜的西瓜,趁着夜深人静,偷偷放在她家的院门口。放完就跑,生怕被人发现。我以为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,是我卑微地、偷偷地表达喜欢的方式。
原来,她一直都知道。知道那些瓜是我送的,知道我那点见不得光又滚烫的心意。
曾小燕看着我傻掉的样子,脸上的红晕更深了,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甜蜜。她轻声说:“头一回,是个月亮很大的晚上,我起夜,隔着窗户缝,看见你个背影,慌里慌张地跑了,像个偷儿。”
她顿了顿,又咬了一小口瓜,嘴角带着笑:“后来,我就留了心。那瓜的纹路,个头,一看就是你李良地里才有的好货色。我爹娘还纳闷,说是哪个田螺姑娘做的好事……我就……我就猜是你。”
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,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了上来。原来我那些自以为隐秘的举动,早就落在了她的眼里。她没有声张,没有拒绝,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份来自土地的最朴实的馈赠,也默许了我这个穷小子笨拙的喜欢。
“小燕,我……”我喉咙发紧,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她把手里那块瓜吃完,擦了擦手,然后抬起头,目光清澈又坚定地看着我:“李良,瓜我尝了,话我也说了。我……我回去了。”
我连忙点头:“哎,回吧,路上慢点。日头毒。”
她“嗯”了一声,转身顺着田埂往回走。走了几步,又停下来,回过头,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传到我耳朵里:“明天……我等你。”
说完,她加快脚步走了,碎花裙摆在热风里飘动着,渐渐消失在田埂的尽头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的背影消失,又低头看看地上裂成两半的红瓤西瓜,空气里还弥漫着那股甜香。刚才发生的一切,像做梦一样。恐惧、责任、惊喜、甜蜜……各种情绪像潮水一样在我心里翻腾。明天,要去面对曾老奎了。一想到那个场面,我的手心又开始冒汗。
但小燕最后那句话,“我等你”,还有她看我的眼神,像是一根定海神针,让我慌乱的心慢慢沉静下来。怕什么?我是个男人,自己做的事,自己担着。小燕这样的姑娘,能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找我,我要是再怂,就真不是个东西了!
那个下午,我再也没心思干活了。坐在瓜棚底下,看着那片绿油油的西瓜地,心里盘算着明天的事。该找谁当媒人?曾老奎那个脾气,空着手去肯定不行,得带点啥?家里还有两只下蛋的老母鸡,还有……对了,就把这个最大的、小燕说甜的那个西瓜带上!
想到小燕说“真甜”时的样子,我心里就像被那瓜瓤甜透了一样,忍不住咧嘴傻笑起来。可笑容还没展开,又被明天的担忧压了下去。就这么一会儿笑,一会儿愁,直到日头西斜,天色擦黑。
晚上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月光从瓜棚的缝隙里漏进来,照在地上,白晃晃的。我爬起来,又走到那个劈开的西瓜旁边。瓜瓤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红润。我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,确实甜,沙棱棱,凉丝丝的甜,一直甜到心里去。这甜味,给了我一些勇气。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。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,换上了一件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。我把那只最肥的老母鸡捆了脚,又精心挑了两个顶大顶漂亮的西瓜,其中一个,就是昨天小燕尝过的那一半(我用瓜叶小心地盖住了切口)。我不能都带劈开的,那不吉利,带一半,是个见证。
媒人我请了村西头的五婶。五婶嘴皮子利索,在村里人缘也好,关键是,她心肠不坏,不像有些媒人光会溜须拍马。我提着鸡和瓜,走到五婶家,结结巴巴地把来意说了。五婶先是吓了一跳,上下打量着我:“良子,你……你真要去曾老奎家提亲?你可知他……”
我重重地点点头:“五婶,我知道。麻烦您了,成不成的,我都念您的好。”
五婶看着我手里的鸡和瓜,又看看我一脸豁出去的表情,叹了口气:“唉,你们这些年轻人啊……行吧,婶子就陪你走这一趟。不过良子,你可想好了,曾老奎那脾气,搞不好真能动手。”
“我想好了。”我说,“动手我也认了。”
五婶摇摇头,没再说什么,收拾了一下,就跟着我往曾老奎家走去。
从我家到曾老奎家,要穿过大半个村子。一路上,早起的村民看见我提着鸡和瓜,还跟着五婶,都好奇地张望,交头接耳。我硬着头皮,假装没看见,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,蹦得厉害。
越走近曾老奎家那气派的红砖院墙,我的腿就越发软。曾老奎正在院门口劈柴,光着膀子,一身疙瘩肉,手里的斧头抡得呼呼生风。看见我和五婶走过来,他停下手里的活儿,拄着斧头,眯着眼睛盯着我们,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。
五婶赶紧堆起笑脸,上前一步:“哎呦,曾会计,忙着呢?”
曾老奎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,目光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身上:“李良?你来做啥?还带着东西?” 他的眼神落在我提着的鸡和西瓜上,尤其是那个用瓜叶盖着的半拉西瓜,充满了警惕和不善。
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,把鸡和瓜放在地上,张了张嘴,还没出声,五婶就抢着说:“曾会计,是这么个事儿……李良这孩子呢,实诚,能干,他……他瞧上你家小燕了,今天特地请我过来,想问问您的意思……”
“放你娘的屁!”曾老奎猛地吼了一嗓子,吓得五婶一哆嗦。他抡起斧头指着我的鼻子:“李良!你个狗日的!老子上次跟你说的话都当耳旁风了是吧?还敢来!还提亲?你撒泡尿照照自己,你个穷种瓜的,配得上我家小燕吗?赶紧给老子滚蛋!不然老子一斧头劈了你!”
他的骂声像炸雷一样,引得左邻右舍都探出头来看热闹。我脸上火辣辣的,血往上涌,但想到小燕,我强迫自己站稳了。
“曾叔,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,“我是真喜欢小燕。我虽然现在穷,但我有一身力气,我肯干!我那十亩西瓜地,今年收成好,我能让小燕过上好日子!我……”
“好日子?”曾老奎啐了一口,“呸!跟你喝西北风啊?滚!赶紧滚!小燕!小燕你死屋里干啥呢?出来看看这个不要脸的!”他朝着屋里喊。
堂屋的门帘动了一下,曾小燕走了出来。她今天穿了一件素净的格子衬衫,脸色有些苍白,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,显然也是一夜没睡好。她看了我一眼,眼神复杂,有担忧,有关切,还有一丝鼓励。然后她低下头,站在门口,没说话。
“爹……”她小声叫了一句。
“你看不见啊?这穷鬼又来缠磨了!”曾老奎怒气冲冲地说,“我告诉你李良,我家小燕已经说好婆家了!镇上的刘干事!吃公家饭的!你趁早死了这条心!”
我心里猛地一沉。说好婆家了?我看向小燕,她猛地抬起头,惊讶地看着她爹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却又被她爹瞪了回去。
五婶一看这架势,赶紧打圆场:“哎呀,曾会计,你看这……孩子们的事儿,好歹也听听孩子的意思嘛……”
“没啥好听的!父母之命媒妁之言!老子说了算!”曾老奎斩钉截铁,“你们赶紧走!东西拿走!别脏了我家地方!”
场面僵住了。围观的邻居越来越多,指指点点的声音也传了过来。我知道,今天这事,难了了。硬碰硬肯定不行。
我深吸一口气,往前走了一步,避开曾老奎的斧头,弯下腰,把那个用瓜叶盖着的半拉西瓜拿了起来,小心翼翼地揭开瓜叶,露出红彤彤的瓜瓤。
“曾叔,”我把西瓜往前递了递,声音尽量放得平稳,“这瓜,是昨天下午,小燕在我地里尝过的。她说……甜。我今天带来,没别的意思,就是想让你和婶儿也尝尝。我李良是人穷,但我的瓜,是咱这十里八村最甜的。我对小燕的心,就跟这瓜一样,实心实意,甜!”
我说这番话的时候,眼睛看着曾老奎,但余光一直留意着小燕。我看见她听到“甜”字的时候,肩膀微微抖了一下,头垂得更低了,耳朵根却红了。
曾老奎大概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出,看着那半拉红瓤西瓜,愣了一下,随即更加恼怒:“谁他妈稀罕你的破瓜!拿走!”
“他爹,” 就在这时,小燕她妈,一个瘦小温和的女人,从屋里走了出来,拉了一下曾老奎的胳膊,“有话好好说,别嚷嚷,让邻居看笑话。” 她又看向我手里的瓜,眼神动了动,“这瓜……看着倒是不错。”
小燕妈平时在家里没什么话语权,但这一句话,稍稍缓和了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。
曾老奎甩开她的手,但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,不过依旧强硬:“瓜好有啥用?能当饭吃?能当房住?李良,我明白告诉你,我闺女不能嫁给你受苦!你死心吧!”
我知道,光靠嘴说不行了。我放下西瓜,挺直了腰板,看着曾老奎,一字一句地说:“曾叔,我知道你看不上我。但我李良今天把话放这儿,我一定能挣下家业,让小燕过上好日子!今年西瓜卖完,我就把瓜棚翻修成砖瓦房!我向毛主席保证!”
我的声音很大,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,不仅曾老奎,连周围看热闹的邻居都安静了一下。
“你……”曾老奎大概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一下,一时没说出话。
就在这时,一直沉默的小燕,突然抬起了头。她脸色苍白,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她走到她爹面前,扑通一声跪下了!
这一下,所有人都惊呆了!
“爹!”小燕的声音带着哭腔,却异常清晰,“我……我怀孕了!是李良的!除了他,我谁也不嫁!”
这句话,比刚才曾老奎的骂声更像一颗炸雷,在人群中炸开了锅!围观的人顿时哗然,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。
“啥?小燕怀孕了?” “天呐!是李良的?” “怪不得……曾老奎这下傻眼了吧!” “真是造孽啊……”
曾老奎的脸瞬间由红变白,又由白变青,他指着小燕,手指抖得像风中的树叶: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啥?你个不知羞耻的东西!你胡说八道!我打死你!” 他扬手就要打。
我一个箭步冲上去,挡在小燕面前:“曾叔!要打你打我!是我的错!不怪小燕!”
小燕妈也赶紧抱住曾老奎的胳膊:“他爹!不能打啊!有事好好说!”
曾老奎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,又看看挡在前面的我,再看看周围指指点点的邻居,那张平时趾高气扬的脸,瞬间垮了下去,变得灰败。他扬起的巴掌,最终无力地垂了下来。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踉跄了一下,靠在院墙上,大口喘着气,眼神空洞地望着天。
完了。他知道,这件事,已经由不得他做主了。姑娘家的名声,比什么都重要。小燕当众说出这话,就等于断了她自己所有的退路,也把他这个当爹的逼到了绝境。
五婶到底是见过世面的,赶紧趁机上前扶起小燕,对曾老奎说:“曾会计,你看这事闹的……生米都煮成熟饭了,再犟下去,吃亏的还是小燕啊。李良这孩子,虽说现在穷点,可人有志气,肯干,对小燕也是真心的。不如……不如就应了这门亲事吧?好歹是条正道。”
小燕妈也在一旁抹着眼泪劝:“他爹,认了吧……小燕的身子要紧啊……”
曾老奎沉默了许久,久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最后,他深深地叹了口气,那叹气声里充满了无奈、愤怒和一丝认命。他看也没看我,只是挥了挥手,有气无力地说:“滚……都滚……老子丢不起这个人!”
说完,他转身踉踉跄跄地走回了屋里,砰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这意思,算是默认了。
我赶紧扶起小燕,她浑身都在发抖,脸上挂满了泪水。五婶和小燕妈帮着把地上的鸡和西瓜拿进院子。围观的人群见没热闹可看了,也渐渐散去,但那些议论和目光,像针一样扎在我们背上。
我知道,从这一刻起,我和小燕,算是被绑在一起了。前面的路,注定不会平坦,风言风语绝不会少。但看着身边虽然哭泣却眼神坚定的小燕,我握紧了她的手。
不管多难,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,得让瞧不起我们的人看看,我李良,能行!
我和小燕的婚事,就在这样一种近乎闹剧而又带着悲壮的氛围中,定了下来。没有三媒六聘的正式流程,也没有大摆筵席的喜庆。曾老奎终究是拉不下脸,婚事办得极其简单潦草。我尽了最大努力,凑钱买了几样简单的家具,把那个破旧的瓜棚勉强收拾出来,糊上新报纸,算是我们的新房。
结婚那天,除了五婶和几个平时还算说得来的乡亲,曾老奎家那边几乎没人来。小燕是自己提着一个小包袱,从家里走过来的。没有唢呐,没有花轿,只有我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,在村口接了她。
她穿着一件红格子的新衣服,是她自己偷偷做的,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悲。当我们俩在瓜棚里,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的时候,我心里酸涩得厉害。我握住她的手,冰凉冰凉的。
“小燕,委屈你了。”我哑着嗓子说。
她摇摇头,抬起头看着我,眼睛红红的,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:“不委屈。以后,这就是咱的家了。”
“家”这个字,从她嘴里说出来,落在我的心上,沉甸甸的。我暗自发誓,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,一定要让这个“家”像个样子。
婚后的日子,比想象中还要艰难。曾老奎虽然默认了婚事,但始终不肯认我这个女婿,路上碰见都当不认识。村里的风言风语一直没有断过,说什么的都有,难听得很。小燕怀孕反应大,吃不下东西,人瘦得厉害。我既要照顾瓜地,又要照顾她,忙得脚不沾地。
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。我伺候那些西瓜秧子,比以前更加精心。我知道,这些西瓜,是我们这个新家全部的希望。我起早贪黑地除草、施肥、浇水,看着瓜一天天长大。
小燕也默默地承担着。她虽然身子不便,但还是尽力把那个简陋的瓜棚收拾得干干净净,给我做饭洗衣。晚上,我们挤在窄小的木板床上,听着田里的蛙声,她会轻轻摸着渐渐隆起的肚子,跟我说些悄悄话,说希望孩子像谁,说等孩子生了叫什么名字。那些时刻,是我们清苦生活中唯一的甜蜜。
西瓜终于熟了。那一年,老天爷帮忙,风调雨顺,西瓜个个又大又甜。我咬着牙,没像往年那样便宜批给瓜贩子,而是借了一辆板车,一天往返几十里路,拉到县城里去零卖。我要卖个好价钱!
县城里竞争激烈,我人生地不熟,一开始并不顺利。后来,我学着别人的样子,切几个大西瓜摆在车上当样品,红瓤黑籽,看着就诱人。我扯开嗓子吆喝:“河滩沙地西瓜!保熟保甜!不甜不要钱!”
我的瓜确实好,又沙又甜,价格也实在,慢慢地有了回头客。我每天天不亮就拉着车出门,顶着星星回来。累是真累,但每天晚上把挣来的毛票数给小燕看的时候,看着她脸上渐渐多起来的笑容,我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一个夏天下来,我竟然攒下了一笔不小的钱。虽然离盖砖瓦房还差得远,但已经足够我们应付接下来的生活,还能有不少结余。
小燕的肚子越来越大,行动越来越不方便。我卖完最后一批瓜,就不再出车,专心在家陪她。我用攒下的钱,买了几只小猪崽,在瓜棚旁边垒了个简单的猪圈,又买了几十只小鸡仔。我想着,光靠种瓜不行,得搞点副业。
日子就在忙碌和期盼中,一天天过去。秋天的凉意渐渐取代了夏日的酷热。地里的西瓜秧子已经枯萎,露出了黄土地。我看着那片曾经孕育了希望的土地,心里盘算着明年开春再大干一场。
小燕临产的日子快到了。我既紧张又期待。那天晚上,我正给她熬小米粥,她突然捂着肚子,脸色痛苦地说:“李良,我……我好像要生了!”
我吓得手里的勺子都掉了!赶紧冲出去喊五婶。农村生孩子,都是找有经验的接生婆。五婶闻讯赶来,又招呼了几个邻居妇女帮忙。
那一夜,瓜棚里的煤油灯亮了一宿。我守在门外,听着里面小燕一阵阵痛苦的呻吟,心揪得像被一只大手攥着,来回揉搓。我在外面来回踱步,手心全是冷汗,不停地祈祷,保佑大人孩子平安。
天快亮的时候,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从屋里传出来!
“生了!生了!是个带把的小子!”五婶推开门,满脸喜气地对我喊。
我腿一软,差点坐在地上。冲进屋里,看到小燕虚弱地躺在床上,脸色苍白,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,但看着旁边那个皱巴巴、红彤彤的小家伙,脸上却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、疲惫而幸福的光辉。
我走过去,握住她的手,她的手冰凉。我看着那个闭着眼睛,小嘴一动一动的小生命,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、巨大的暖流和责任感。这是我的儿子,我和小燕的儿子。
“小燕,辛苦了。”我哽咽着说。
她摇摇头,看着我,笑了,眼泪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:“看看孩子,像你。”
我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柔软的小家伙,他那么小,那么轻,在我怀里动了一下。那一刻,所有的辛苦、委屈、别人的白眼,都变得不重要了。我有家了,一个真正完整的家。
我给儿子取名叫“李望”,希望的望。希望他将来能有出息,希望我们这个家,充满希望。
有了孩子,生活更加忙碌,但也增添了无数的乐趣。小燕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,脸上渐渐丰润起来,有了做母亲的那种柔和的光泽。我忙着照顾小猪小鸡,盘算着明年开春的土地。虽然日子依旧清贫,但瓜棚里充满了孩子的哭声笑声,有了浓浓的烟火气。
孩子满月那天,我硬着头皮,提着一篮子红鸡蛋,去了曾老奎家。不管他怎么对我,他毕竟是孩子的外公。
我站在他家院门口,心里忐忑不安。小燕妈听见动静出来了,看到我和篮子里的红鸡蛋,愣了一下,眼圈就红了。她接过篮子,小声说:“进来坐坐吧?”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摇摇头:“不了,婶儿,就是……给孩子送点红鸡蛋。小燕和孩子都挺好。”
小燕妈点点头,擦了擦眼角:“好,好就行……你……你也注意身体。”
我正要转身离开,堂屋的门帘掀开了,曾老奎走了出来。他看起来老了一些,背也有些驼了。他看了我一眼,目光复杂,又看了看小燕妈手里的篮子,沉默了一会儿,瓮声瓮气地说:“站着干啥?进来喝口水。”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!他……他让我进去?
我愣在原地,没动弹。小燕妈赶紧拉了我一下:“你爹让你进去呢,快进来吧。”
我晕乎乎地跟着进了屋。曾老奎坐在八仙桌旁,没看我,自顾自地卷着旱烟。屋里气氛很尴尬。
小燕妈给我倒了碗水,又拿出些花生瓜子。“孩子……取名了没?”她问。
“取了,叫李望。希望的望。”我赶紧回答。
“李望……好,好名字。”小燕妈念叨着。
曾老奎一直没说话,直到卷烟抽完,他才磕了磕烟灰,抬眼瞥了我一下,依旧是硬邦邦的语气:“地……都收拾完了?”
“哎,收拾完了。”我连忙应道。
“明年,还种瓜?”
“种!今年攒了点钱,明年想多包两亩地,种点新品种。”
“嗯。”他又嗯了一声,不再说话。
坐了不到十分钟,我就如坐针毡,起身告辞。曾老奎也没留,只是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,突然说了一句:“……有空,让孩子他娘,抱孩子回来看看。”
我的脚步顿住了,心里百感交集。这句话,虽然说得别别扭扭,但意味着,他终究是松口了。
“哎!知道了,爹!”我回头,响亮地应了一声。
走出曾老奎家,冬天的阳光照在身上,暖洋洋的。我看着远处河滩上我那片已经休憩的土地,想象着来年春天,新的瓜苗破土而出的景象。
回到瓜棚,小燕正抱着孩子喂奶。我把去她家的事跟她说了。她听完,低着头,久久没有说话,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孩子的襁褓上。但我知道,那是开心的眼泪。
冬天来了,万物萧瑟。但我们这个小小的瓜棚里,却因为新生命的到来,而充满了暖意和希望。我搂着小燕,看着怀里熟睡的儿子,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。
路还长,日子还苦,但我不怕了。因为我有了要守护的人,有了拼下去的动力。就像那西瓜,无论土地多么贫瘠,只要肯用心浇灌,总能结出最甜的果实。
来年春天,我的西瓜地里,一定会是一片更加旺盛的绿色。
发布于:陕西省香港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配资平台排名德国DAX指数涨0.34%
- 下一篇:没有了